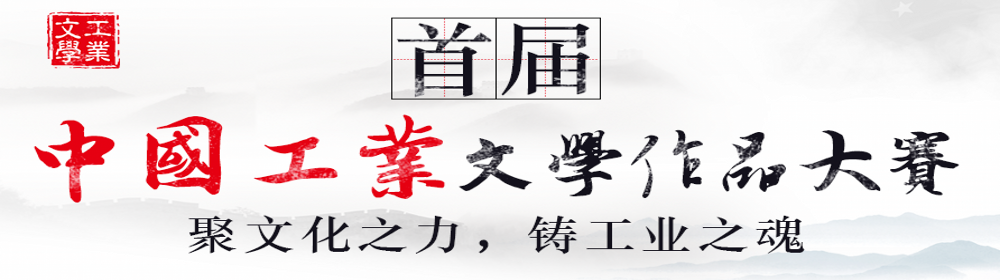老屋院中的捶布石
2025-12-20每年春节,我总带着妻儿赶在年关的尾巴上回趟老家,去半山的老屋走一遭。老屋离住处不过三里地,山路弯陡,荒草早已没过膝盖。它静卧在一片枯黄里,像个沉默的老头守着满院冷清——院门洞塌了一角,半人高的杂草疯长,七孔窑洞透着沉沉死气。可记忆里的一切都鲜活得很,像有人在耳边轻诉从前。只要脚踏进院子,奶奶的笑声、父母忙碌的影子,便会穿过时光的尘灰,清清楚楚浮在眼前。
我总爱里里外外转几遍,手指抚过斑驳的墙,触到的是岁月透骨的凉。那天在奶奶住的拐窑,望着塌了的空灶台发呆时,窗口一缕细光忽然刺破灰蒙蒙的空气,直扎进眼里。顺着光望去,院子墙角的草堆里,有个青灰色的东西蒙着厚尘,像被遗忘的旧梦。蹲下身,伸手一层层拂去浮尘,指尖触到粗糙石粒,渐渐的,光溜溜的石面露出来,带着年月打磨的温润亮泽——是那块捶布石,那块在我生命里刻满故事的捶布石。
没人说得清它的来历,只听村里人讲,是桥陵四方台的石灰石,硬得很,风吹雨打留不下啥印子。四四方方,敦敦实实趴在院角落,像头闷不吭声的老黄牛,稳稳当当。石面被经年累月的捶打磨得光溜透亮,没一丝裂纹,岁月的刀斧在它身上,仿佛只留下温柔的印子,连石缝里都藏着洗不掉的皂角香。
小时候,这捶布石是奶奶和母亲最贴心的“老伙计”。那时候的日子,慢得像老座钟的摆。晴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拎着一大盆衣裳被褥,在捶布石旁的瓷盆里倒上滚烫的水,捏一把砸碎的皂角,让衣裳在白花花的泡沫里泡着。而后挽起袖子,拿起沉甸甸的枣木棒槌,高高举起,再重重落下。“梆——梆——梆——”脆生生的声响混着窑背酸枣树的鸟叫、远处的鸡啼,成了童年最常听的晨曲。母亲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,滴在捶布石旁的土地上,洇出小小的湿痕。
奶奶的动作比母亲慢些,也柔些。她捶的多是贴身小衣、孩子的尿布,捶几下,就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捋平褶皱,指腹摩挲布料,再凑近些,眯着老花眼细看,怕哪里没捶干净。阳光透过门前刺槐叶的缝隙,碎金子似的洒在她们身上,镀上暖乎乎的光晕。捶布石上的水珠溅起又落下,湿痕顺着石纹流下来,在地上积一小洼水,映着蓝天白云。我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,看衣裳在棒槌下渐趋平整,看泡沫顺着石纹缓缓流淌,闻着皂角的清香,心里安稳得很,好像这世上所有吵闹,都与这小院无关。
七岁那年夏天,蝉鸣格外聒噪。母亲刚洗完一床白底蓝花的床单,平展展铺在捶布石上,转身进屋提水。我瞅准机会,踮脚抓起那根沉甸甸的棒槌——实木的清香里,是硌得手心发疼的沉。学着母亲的样子把小胳膊抡得老高,使出全身力气砸下去,可小胳膊哪掌控得住蛮劲,棒槌不偏不倚砸在左手指上。
“哇——”钻心的疼涌上来,眼泪噼里啪啦掉,血从指甲缝渗出来,染红了白床单。奶奶和母亲听见哭声慌忙跑出来,脚步声急得像打鼓。母亲一把抱起我,手忙脚乱查看手指,眉头拧成疙瘩,嘴里不停念叨:“咋这么不小心,疼不疼啊娃?”小脚奶奶转身冲进屋翻箱倒柜找布条,嘴里嗔怪母亲:“你咋就没看好娃!”声音里带着急,手指却格外轻,小心翼翼用布条缠我的手指——那布条上,有阳光晒过的暖,还有淡淡的皂角香。从那以后,我再没碰过棒槌,可那天的疼,还有奶奶母亲紧张的样子,却成了记忆里抹不掉的印子。
夏日傍晚,是捶布石最热闹的时候。忙了一天的奶奶和母亲,搬着小板凳坐在旁边乘凉。晚风悠悠吹着,带走燥热,带来院外杏林的沙沙声。我们姊妹几个挤在奶奶身边缠她讲故事,她摇着蒲扇,扇出阵阵凉风,讲牛郎织女隔天河相望,讲孟姜女哭倒长城,讲那些老掉牙的民间传说。母亲在一旁借着夕阳余晖纳鞋底,针线翻飞,偶尔插上一两句话,声音柔得像晚风。
星星慢慢爬满夜空,亮晶晶的像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。我们干脆躺在捶布石上,石面带着白天晒过的余温,贴在背上暖融融的,舒服得让人犯困。数着星星,听着故事,连晚风都变得温柔,悄悄拂过脸颊带走疲惫。有时邻居家的小孩也跑过来,我们就在捶布石周围玩跳房子、捉迷藏。它成了我们的“大本营”,藏在身后,好像就躲进了最安全的地方。
日子一天天过,时光跑得飞快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,村里新房越盖越多,红墙黛瓦气派得很。老人们慢慢走了,变成山间一抔土;年轻人大多外出挣钱,去追更远的地方。老屋渐渐荒了,院里的草一年比一年旺,可那块捶布石,还安安静静趴在角落,光溜、坚硬,好像从没被时光改变——它见过奶奶母亲捶衣裳的忙碌,听过我小时候的哭与笑,看过一家人围坐乘凉的暖,也瞧着老屋从热热闹闹到冷冷清清。
它就那么守着老宅,守着荒院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风吹雨打,日晒雨淋,啥也不说,只默默立在那儿,像在等回来的人,等那些被岁月埋起来的故事再被想起。石面上的光被风雨冲得淡了些,可还是温润的,像奶奶的手,轻轻摸着每个回来的脚步。
如今每次回老屋,我都会蹲在捶布石旁,轻轻抚摸它光溜的石面。指尖触到的,是岁月的温度,是亲情的暖,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这哪是块普通的石头?它是老一辈人勤谨实在的刻痕,是老屋兴衰的见证,是我们对老家最深的牵挂。
天慢慢黑了,山风卷起院里的落叶和草屑打着旋儿飞。我站起身,最后看一眼捶布石,它在夕阳余光里闪着温润的光,像颗嵌在时光里的琥珀。转身时我知道,不管走多远、过多久,老屋院中的捶布石,都会在记忆里、在老家的风里,守着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,守着一份不会褪色的暖。(编辑:王根平)
.jpg)